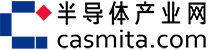2019年11月23日,香港特別行政區(qū)區(qū)議會選舉前一天,澳大利亞上演了一出教科書般的“干預選舉”丑?。?



這天一早,該國《時代報》(The Age)、《悉尼先驅晨報》(Sydney Morning Herald)和澳洲九號電視臺(The Nine Network)新聞節(jié)目“60分鐘”一齊拋出“中國間諜滲透香港 投誠澳洲求庇護”的“大新聞”,香港、臺灣地區(qū)一眾“毒媒”隨即跟進,讓本就復雜詭譎的香港局勢更加混亂。
雖然中國迅速有力地進行了反制,第一時間證明這完全是個子虛烏有的假新聞,但惡劣的影響已經造成,對次日選舉的沖擊難以估量。

經公安機關核查,當事人王立強實為在逃詐騙犯
這場“表演”,是澳大利亞媒體近年來一貫作為的最典型案例。近年來,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以來,澳大利亞頻頻向中國發(fā)難,政界、媒體競相抹黑中國,煽動反華、恐華情緒,幾近無所不用其極。雖然美西方主流媒體在對華報道上基本都采取負面、雙標做法,但鮮少有哪國媒體像澳大利亞這幾家這樣,跳得這么高、叫得這么響。
澳洲媒體的“十宗罪”
過去一年,美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的“口誅筆伐”達到了一個新高度。在它們的報道中,你很難看到一句說中國好的話,香港修例風波、新疆“人權問題”、華為5G、網絡攻擊、知識產權等話題被反復翻炒,真可謂生命不息、抹黑不止。除了這幾項“規(guī)定動作”,澳媒還“自發(fā)”地翻炒了一大堆的“自選動作”,比如指責中國干預澳大利亞政治。
從2016年開始,以澳大利亞廣播公司(ABC)為代表的一群澳媒,就開始渲染“和中國有聯(lián)系”的企業(yè)及個人向該國政界輸送政治獻金,“輕而易舉地成為了外國捐款的最大來源”。 2017年6月,澳大利亞安全情報機構親自為這些報道背書,宣稱政治捐款的金額超過550萬澳元,“兩位著名華商有可能是中國政府代理人”。 當年11月,澳大利亞工黨參議員山姆·達斯提亞里(Sam Dastyari)因涉嫌收受“中國獻金”被迫辭職,工黨黨首比爾·肖頓(Bill Shorten)也被卷入非議。澳大利亞金融評論(AFR)則“披露”與中國談成了一項貿易協(xié)定的前澳洲貿易部長安德魯·羅布(Andrew Robb)收到了“一名中國富豪年薪逾65萬美元的兼職顧問合同”。
澳媒還指責中國在澳洲政壇直接安插代理人。
2017年12月,《澳大利亞人報》(The Australian)在頭版刊文稱,澳大利亞情報機構已經確定了“十名與中國情報部門有關聯(lián)的地方和州政治候選人”,這是“中國干涉澳大利亞民主體系計劃的一部分”。 2019年9月,澳大利亞自由黨女議員、澳洲首名華裔議員廖嬋娥(Gladys Liu)因為涉嫌“通共”,淪為澳媒的眾矢之的。 同年11月底,“王立強案”的畫皮被戳穿后,《時代報》、《悉尼先驅晨報》和“60分鐘”不僅不就此收斂,反而更加瘋狂地大炒起“中國情報機構試圖在澳洲議會安插一名特工”,而且這回學聰明了,直接搞了個死無對證。

澳大利亞議會(資料圖)
憑空造謠、無中生有仍嫌不夠,澳媒還演示了什么叫“欲加之罪,何患無辭”。
2017年3月,中國駐澳總領事邀請澳洲當?shù)厝A裔居民和公民來到中國使館,希望他們在即將到來的中國領導人訪問期間幫助塑造公眾輿論。這個再正常不過的公關活動,卻被外媒解讀成了“中國政府直接——而且往往是秘密地——參與澳大利亞政治活動的一個例子”。
澳媒“腦回路清奇”可遠不止這一例。
2019年5月澳大利亞大選前,ABC大肆炒作微信上“隸屬于中共的賬戶”嘲笑聯(lián)盟黨政府、詆毀澳大利亞,為“中國干涉之鐵證”。這些賬戶是何方神圣?打開報道一看,“鐵血軍事”明晃晃映入眼簾,下面則是《環(huán)球時報》,以及一幅“難民全部綠卡!共享澳洲盛世!”的網友P圖。這是認定了讀者都不懂中文嗎?
澳媒強加的其他罪名還包括染指澳洲新聞報道(“罪名”是一家公司在澳洲的報紙上發(fā)宣傳中國的廣告)、壓制出版(一份書稿因為水平問題沒有出版商肯收,也成了中國的鍋)、攪動澳大利亞學術自由(因為中國留學生自發(fā)同亂發(fā)涉華錯誤言論的教師辯論)、以及壓制香港、臺灣的聲音(中國留學生舉行了愛國愛港、反對臺獨的游行)??偠灾С种袊褪?ldquo;有罪”。
就連中國對澳大利亞經濟的貢獻都成了“罪”。在澳媒口中,澳大利亞經濟對中國的“過度依賴”帶來了威脅,互惠互利的經濟關系,成了中國對澳政治施壓的“陰謀”。
自2009年以來,中國就一直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雙邊貿易伙伴,2019年,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份額從2018年的34%達到了創(chuàng)紀錄的38%,即1170億澳元,高于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(qū)。此外,中國留學生已被公認為澳大利亞教育產業(yè)的最大貢獻者,每年為澳大利亞經濟帶來320億澳元的收入。普華永道首席經濟學家杰里米·索普(Jeremy Thorpe)表示,如果中國經濟急轉直下,澳大利亞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會減少3至5個百分點。
按理說沒有人會跟錢過不去,但澳大利亞偏偏就要在財神爺頭上動土。近年來,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幾乎沒有不引起爭議的,租借達爾文港、收購澳洲電網(Ausgrid)、投標天然氣管道、參與興建5G,連收購一塊私人養(yǎng)牛場都能驚動堪培拉。
澳大利亞沒有簽署任何“一帶一路”諒解備忘錄。因為杞人憂天般的“中國施壓”而拒絕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,澳大利亞偏執(zhí)、敏感到了如此程度,真是令人震驚。對此,澳媒的選擇性報道居功至偉——它們眾口一詞地竭力渲染虛無縹緲的“中國威脅”,卻只字不提中國投資帶來了多少看得見、摸得著的好處。
這其中的原因,除了“有色眼鏡”和意識形態(tài)之外,實在找不出別的解釋。
極其惡劣的負面影響
澳洲媒體對華報道的傾向如此之歪,澳洲政府難辭其咎。
2019年10月,莫里森政府最資深的人物之一、澳大利亞內政部長彼得·達頓(Peter Dutton)大放厥詞,公開聲稱中國與澳大利亞的價值觀“格格不入”。ABC表示,這是“迄今為止澳洲聯(lián)邦政府部長對中國構成的威脅發(fā)出的最強硬的言辭”。就連這位總理本人,也第一時間對子虛烏有的“王立強案”表示“令人深感不安和困擾”。
類似言論,近幾年來澳大利亞一抓一大把:
著名對華鷹派、自由黨議員兼國會情報安全委員會主席的安德魯·哈斯蒂(Andrew Hastie),敦促澳大利亞政府和公眾認識到“中國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民主和安全威脅”,并將西方對中國的容忍與對納粹德國的綏靖相提并論。 2018年6月,澳大利亞通過《反外國干預法》,毫不掩飾地指向中國(馬爾科姆·特恩布爾臭名昭著的“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”言論,正是為該法而發(fā))。

一些澳洲政客幾乎毫不掩飾對中國的敵意,似乎對中澳關系日趨惡化毫不擔憂。政界風向如此,媒體只會更極端。
這些極端言論的毒素已經蔓延到了公眾輿論中,整個澳洲社會對“北京的政治野心”和“中國間諜”杯弓蛇影,草木皆兵。
2019年澳大利亞羅伊研究所(Lowy Institute)的民調顯示,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態(tài)度全面趨于強硬,44%的受訪者認為,在決定允許哪些外國公司為重要服務提供新技術時,“保護澳大利亞人免受外國政府的入侵”應該是政府的首要任務。只有32%的受訪者表示,他們“非常”或“在一定程度上”相信中國會“負責任地行事”,這一比例較2018年下降了20個百分點,跌至羅伊研究所民調史上的最低水平。
安德魯·哈斯蒂宣稱,自己的辦公室已經被來自澳洲全國各地的電子郵件、電話、甚至是手寫信件淹沒了,這些人都在表達他們對“中國在澳大利亞行徑”的憤慨和焦慮。“傅滿洲”好似又出山了。
但澳大利亞從這種極端偏頗、負面的媒體立場中獲益了嗎?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公眾輿論的惡化顯然影響澳大利亞對中國投資和學生的吸引力。
事實上,悉尼大學副教授薩爾瓦托·巴邦斯(Salvatore Babones)承認,中國學生的入學人數(shù)已經開始下降,截至2019年5月底,當年澳大利亞中國留學生的入學人數(shù)僅增長了2.4%。同樣,英國《金融時報》記者杰米·史密斯(Jamie Smyth)也指出,“目前已經出現(xiàn)了放緩的跡象,第一季度發(fā)放的中國學生簽證數(shù)量下降,悉尼麥考瑞大學(Macquarie University)實施了預算削減,至少部分原因是國際學生數(shù)量下降。”
政治領域的負面影響更加直接。在此前的種種“作死”操作拖累之下,即使當前的堪培拉政府試圖改善雙邊關系,也會發(fā)現(xiàn)困難重重。前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效銳(Geoff Raby)甚至認為,中澳關系正處于兩國自建交以來的最低點,因為自2016年以來,還沒有澳大利亞總理訪問過中國(事實上,特恩布爾那次也是為了參加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,而非專程訪華)。
要改變這一局面,澳大利亞媒體必須率先做出改變,因為正是他們挑起的單方面指責,導致了中澳關系急轉直下、跌入低谷。
但是,澳媒會改變嗎?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。
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“王立強案”。無論是勁爆程度、時機選擇還是聯(lián)動水平,這枚“輿論炸彈”都堪稱頂尖,絕對是經過了精心籌劃,專門沖著香港區(qū)議會選舉而來,下手穩(wěn)、準、狠,影響格外惡劣。
這已經不能用一般的“宣傳效果”來衡量了,它將脫離新聞史,被列入國際關系史范疇,堪與那封引發(fā)普法戰(zhàn)爭的“俾斯麥電文”相媲美(BBC炒作鄭文杰也是如此)。很難想象,沒有幕后黑手的指揮、單憑這幾家媒體自己,能夠制造出如此爆炸性的效果。
這起事件足以證明,部分澳大利亞媒體已不再是普通的“反華媒體”那么簡單了,而是已成為“五眼聯(lián)盟”宣傳機器中的一支“特種部隊”,與美西方反華政治、情報勢力高度協(xié)同、密切合作,專門在敏感時點拋出精心炮制的“炸彈”,作用非一般謠言可比,目的就是打擊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家利益。
對于這些媒體,也已不應再用傳統(tǒng)的、看待普通外媒的眼光和方式來對待,而應正視其真實面目,堅定進行有力揭批和反制,才能守住中澳關系的底線。